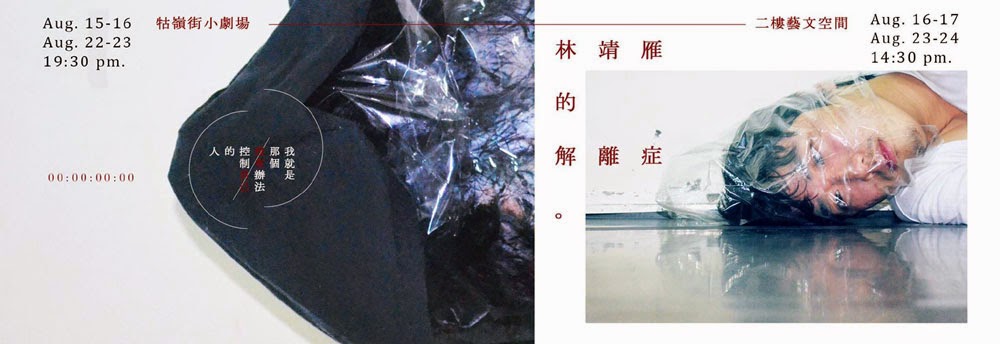你覺得這個世界上有聖人嗎?我覺得有喔。
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,在一個公共空間裡,那個人談論著這個國家目前的各種危機,而他以外的所有人,專心聆聽他的每一句話,每一隻眼睛都不願意眨一下,深怕在一眨眼之間,他就會消失。
一開始吸引我的,是那個區域散發的一種氣氛,是那種如果拿著電視上的磁場分析儀,會看見金色光芒的那種氣氛,其實說也奇怪,為什麼「好」的磁場是金色的光,而不是別的顏色,說不定金色的光不是什麼「好」磁場,是……想睡覺的磁場。總之,是那樣的氣氛,我在一旁窺視著,直到一個年輕人走向我,問我願不願意參與一個改變世界、改變社會的討論,其實我只是好奇而已,便被他拉進一個座位,他表現得好親暱,好像我跟他認識已經超過十年,但我明明只跟他說了一句話。
很快我就有疑惑了,這好像不是什麼討論,這些人只是在聆聽那個人所講的話而已,的確,那個人真的很棒,只要聽了他講三句話,就會忍不住一直聽下去,有條有理地闡述著國家的各種危機,每一種都值得花上好幾十年做研究,但那個人能夠針對一個主題,說得很簡單,簡單得連我這種本來根本不知道要改變社會什麼的人都突然覺得,這一切都應該被改變一下,但弔詭的事情是,當那個人結束這場討論之後,也許我根本不記得他講得任何一句話,而我只會記得,要相信這個人,並……也許跟隨他的腳步,參與他策劃的行動。
後來有一個時間在討論,說討論,其實也只是問那個人問題而已,每個人都非常積極地舉手,問著各式各樣的問題,針對那個人剛剛演講的主題,說真的,我並不清楚,這些人是不是問了真的和那個人剛剛演講的主題有關的問題,因為很多年以後,我依然記得一個有點肥胖的女孩激動地落淚,並說了一個他的朋友被警察抓走的故事,然後問了一個我已經忘了是什麼的問題──我好像真的忘了很多事情,很多細節,也許那些都很重要──而那個人很熱心的回答胖女孩的問題,胖女孩很感激。
會後,人潮慢慢散去,而我只是呆坐在那個座位上,因為它坐起來很舒服,我想我可以繼續坐在這看書,而那個一開始拉我進來的年輕人又走向我,問我感覺如何,是不是有什麼話想說,其實我真正想跟他說的是「他媽的,你一開始為什麼要打擾我一個人窩在我的地方看書,害我少看了30頁。」但我沒這麼說,因為我現在想不起來當時到底在看什麼書了,也許一點也不重要。總之,我回絕他,並向他道謝,便離開了,離開前他給我他的聯絡方式,說真的,我沒有特別想聯絡他,因為他身上有股我並不喜歡的氣味──簡單說就是有點臭。
我走出外面,繞近我習慣行走的小巷子,那邊沒什麼人,但是很多蟑螂,是一個平時店家堆積垃圾的地方,在那裡,我看見了剛才演講的那個人。
他正在一邊抽煙,一邊小便,對著那堆垃圾,撒著尿。
說真的,我有點驚訝,驚訝於這個人的……兩面性,但我猜他應該比我更驚訝,因為這種人大概一點也不想讓人看見他一邊抽煙一邊小便,或者說不定他根本就是想拿那團燒紅的煙草去燙他的排泄器官,但他很鎮定,他看著我,繼續小便繼續抽煙。
他說:「我知道你,你是剛剛唯一沒有問問題的人。」他還在小便。
他抽了一口煙,噴出去,他說:「怎麼樣?現在有比較想問問題嗎?」他還在小便。我開始幻想他的尿袋可能比一般人更大,或者他的肌肉壓力比一般人小。他甩動著他的排泄器官,一直甩動。
我有種被挑釁的感覺,於是我走到他的旁邊,他也不躲也不閃,繼續甩動他的排泄器官,我看見一支蟑螂走進他的皮鞋底,接著飛也似地轉頭跑去。
我掏出我的排泄器官,也開始小便。
他說:「好樣的。」
接著他,他又繼續小便了。
我想他根本不是人,應該是狗或什麼之類的。
一個問題在我腦海浮現,我脫口而出。
你覺得這個世界上有聖人嗎?
他轉過頭,看著我,眼睛裡有著比好幾個小時前在演講台上高談闊論的鬥志,更高的精神,我知道我問對問題了,一個絕對的問題。
他開始高談闊論,關於歷史上的聖人,以及人類對於神聖的定義與看法,他到底講了多久我已經沒有感覺了,我只記得他在講聖人時,他的尿從來沒有間斷過,尿濕了一整包的垃圾袋,蔓延在整個餿氣沖天的小巷子裡,淹死了每一隻經過的蟑螂,而我也一直沒有把我的排泄器官收好,並任由他的尿液沾滿我的鞋子褲子。
最後他說:「其實這些都不重要,我想你也知道。」他終於尿完了,他繼續好幾個小時前甩動排泄器官的動作,而我也是。
他說:「重要的是,我們現在要進行的事情,我和你,還有另外幾個人,我再介紹你們認識。」
什麼人?誰?什麼事情?我為什麼要加入?
他說:「你會感興趣的,我們要玩一個遊戲,一個很長很長的遊戲。」
什麼遊戲?
「聖人遊戲。」
[B/6]